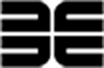1993.02.13 - 1993.03.14
307、308、309、310、311
看過袁旃的水墨畫作,一時感受良多,有如初夏新月,境界清新。
美術創作的理念,源自於作者生活背景的孕育。在諸多的美術形式中,有人喜愛純樸的、複雜的或幻夢的等等不一而足,然在創作的過程中,必然有其時空因素的影響,包括學習的過程,表現的技巧與目的,當然因爲各人秉賦不同,而有不同的面目出現,尤其在繪畫的製作上,更令人有目不暇給的急促感。倒不是美感的多樣性使人目炫,或是環境的需要有所欠缺,而是美術品隨著社會發展,有大幅度的改變,其美學詮釋的範圍更爲廣泛了。
説到社會的發展所牽動的美學理念,足夠使從事藝評工作者大開眼界,尤其台灣地區所承受的文化濃度,正是中華文化衍生的新境,包含了傳統美學的厚植,其承受數千年來農業社會的根葉,加上四十年來,國際文明的浸淫,舉凡資訊的取得與輸入,必在原有人文湖泊中,引起巨大的漣漪,移動時彩光閃爍,耀目的是再生的能源,正導引中國人健壯的腳步前去。畫家尋著這一道光芒,正熾熱情,思考著要吐露的美學觀點,就是他們創作的全部。
因此,做爲一個是晝家的人,必須了解時代的意義與環境的條件,選擇一份篤實而實際的創作方向:他可以審視社會發展的本質,乃存在人類生活的眞切,也可以環視國際互動的文明,究竟在何處發光,屬於內在性或説是主觀的情思,應該被匯集在恒常的形質上,長遠而深切的体現,是在尋求有面目的人。有面目並不足以代表優雅,必須可以感動人的表現,才算有生命力,這也是對用心的人説的。袁旃的情況,正投入在這項核心中,除了有一個良好的家庭外,才智使她一路上暢通,除在師大的學習精彩外,遠赴西歐求學,所立基的力量,不僅使她有傲人的學經歷,在中西藝術理念相融之時,其廣用的藝術表現符號,超越了不同人種的阻隔,毅然在專業工作的崗位上,作一次重大的決定,那便是現代性的再現,是在她深厚的民族情感之上。她了解文化智慧,是在先人們留下的經驗,也是一再咀嚼品咮的憑藉,是唐宋的自然之道也好,或是文明的寫意也行,不能忽略的是繪畫不是單一的水柱,而是萬流歸海的浪花,隱隱聲奢渾厚清遠,鼓噪在畫面上,有股人間至情至性的吶喊。
我們看袁旃的畫作,筆墨只在説明繪畫的要素,形質的表現才是她創作的重點,是文人氣質也好,或是專家的純釋,畫過人性的眞實,不僅是美好的感觀,而是思路上的意見,可看可思可感在古人是説過了,可遊可居可行也是山水畫的畫境,但除了這些諸多的「可」外,袁旃似乎又多了一層可生可存可貴的意味,述説著遠離人群的清明,也拉開了苦悶的現寅,對於未來的世界,能刻意裝飾的是期待的理想,畫境的深遠,便是理想的充實,在人格投射的是晝品的提昇。再者,是袁旃的水墨畫,應用東方美學熟悉的表現技法,從中提煉新意,是項令人鼓舞的事蹟。新意是在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後的性靈 ,也是她近卅年研習中西美術的結果。尤其在故宮服務,日月與文化精粹爲伍,必能受之愛之而相濟,取歷史所轅換的契機,補足藝術的生命體,其中定型取勢,或氣盛撲面,合乎天地之性,萬物之情。繪畫的表現,貴在此一新意之中。
袁旃接受學院式的教育,也保持藝術的童心,更能把握美術本質的体驗,説是得意忘象的性情製作,或説是隨興點染表現,俱備多樣性的才情,原本是學藝莕必備的條件,只要能握住一絲眞切,美感的獲得,應該是含情在毫,宗寓筆墨 。我們看到的是,元晝的精華、宋畫的丘壑,常被宇宙造化所震懾,也看到印象畫的組成,現代畫的思維,屬於思考性的遛輯,雖然不是絶對的二分,卻不易使二者相融,當然,越過這一層次的境界,便是自明性的堅持了,袁旃便是掌握這一趨勢的創作者,因此,她的畫作充滿了時空交集的痕跡,既深且廣,或許在敘述著本世紀的心聲,也是自己性靈的呢喃,藝術家自明自生,乃藝術品創作的重要泉源,袁旃的作品充滿了生命力,便來自她生活的眞寅,期這一眞寅感染這個時空,也照耀人生的價値。(來源:展覽說明書)
袁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