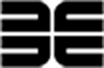1993.09.11 - 1993.10.03
B02、B03
大多數台灣的藝術家都曾走過「學院」這條路,並在美學、美術史、色彩學之薰陶下,堅信創作藝術品必須遵循此項眞理——優美的造形、色彩、構圖,嫻熟的技巧以及獨特而穩定的風格。我個人就在這樣的環境裏,很「道地」的一路走了下來,同時頗能習慣性地忽視少數學院藝術的背叛者或前衛藝術的追求者——那些被視爲不務實際、自以爲是的實驗者。但是當個人在藝術的領域內不斷努力,使作品更符合前述的眞理時,卻發現藝術的精神正逐漸遠離;這現象對一個學院藝術的模範生而言,自是難以容忍。於是在年過而立之際,放棄了近十年的安定敎學創作生活,攜妻帶子投入另一個國度。取經的甘苦總能讓理念獲致印證之後的滿足感取代。沈浸在西方的環境裏並不足以引起我對其藝術形式的崇拜或仿效,卻不免因其藝術家在艱困但自由的空間裏竭力追尋個人藝術的最高理念,而心懷敬佩。
旅英三年深深體會到,眞正的藝術家與優秀的藝術品未必能獲得立即的掌聲,卻必定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創作」唯有出自內心的一片眞誠,斷無迎合、遷就、取巧的可能。同時,我意外地發現,台灣這塊土地在我遠離她時,竟顯得分外淸晰、迷人。這份割捨不去的情結令我相信,不論以何種方式創作,只要基於內在的熱情,與個人生存的空間緊密結合,作品必然蘊含本土的生命力,這或許是此地藝術家未來在國際藝壇獲得肯定的可能途徑。
初抵異邦的驚訝、讚歎和困惑非常直接地烙印於早期的作品中,在舖陳與堆疊下遁入了超現實,該是我彼時之境遇最鮮活的寫照。隨著適應的改善,創作也因邁入思考期而接近中斷;在一個藝術家的生涯中,這種現象必然持續出現,但是對一個「學人」來說,卻成爲沈重的負擔,歸因於自我的期許和挑剔。直到某天,硏究所一位同學提醒我:「你的白髮好像增加不少。」才意識到,我竟然在牛角尖裏,企圖將整個生命歷程當作電影一般,在兩個鐘頭內演完:這承襲了台灣人普遍缺乏歷史感而熱衷於立竿以見影的習性因此表露無遺。相較之下,西方人對藝術源遠流長的本質多有根本的認知,卻往往在時間的緩步推移中,此起彼落地綻放美麗的花朶。
返台之後,我將累積數年的心得略作整理,並在心理上取得相對的平衡,即著手目前的系列作品——「門」。我深感興趣的是它在人類世界所扮演的角色,是觀念的?亦或現實的?由於創作的重心在於透過心靈詮釋視覺,帶有濃厚的實驗特質,因此「形式」和「內涵」的爭議性也明顯昇高;兩者的拿揑在分寸之間,卻可能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這恐怕也是本地藝術家在面臨藝術的社會功能這類
難題時,需要謹愼思考的。(來源:展覽說明書)
蘇志徹